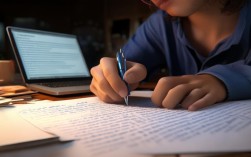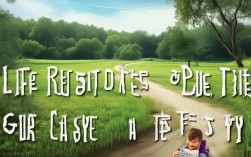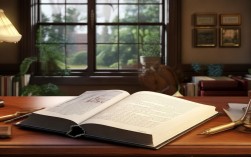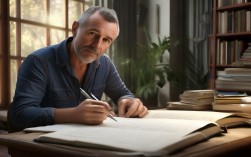字未必如其人
自古以来,“字如其人”的观念便深入人心,仿佛一个人的笔墨痕迹,是其品德、性格乃至灵魂的直接投射,人们常说“见字如面”,相信透过字里行间,便能窥见书写者的风骨与气度,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,这一论断未免失之偏颇。我以为,字未必如其人,它更像是一件经过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承载着书写者的技巧、心境与时代烙印,而非其人格的绝对镜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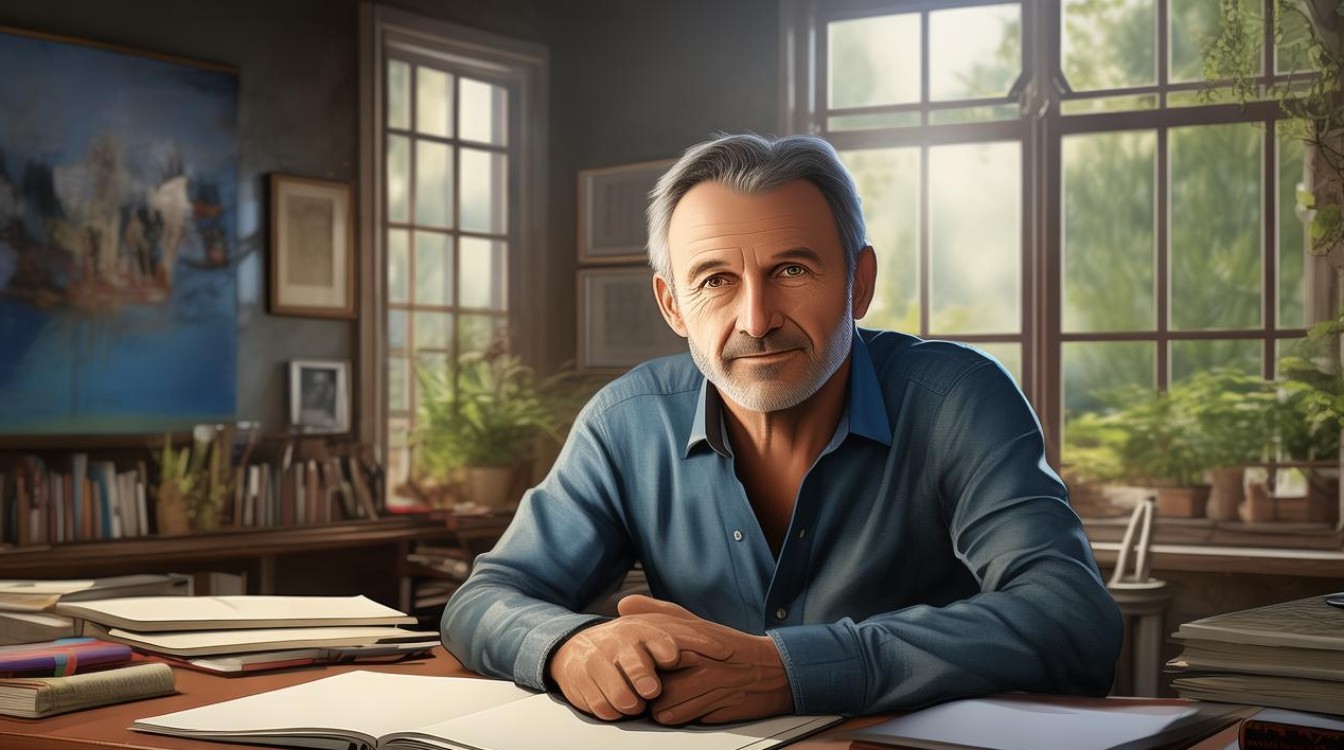
书法是一门技艺,其背后是千锤百炼的功夫,而非天生的品格。 书法的诞生,源于对法度的遵循与对笔墨的驾驭,一个书法家,尤其是初学者,必须从临摹碑帖开始,日复一日地练习横、竖、撇、捺,力求达到形神兼备,在这个过程中,书写者首先要“忘我”,要放下自己的个性,去模仿古人的笔法、结构和气韵,正如颜真卿的雄浑大气,是在经历了家国之痛、人世沧桑后方才形成的;王羲之的飘逸洒脱,是在魏晋风度的熏陶下自然流露的,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,我们所看到的“好字”,往往是书写者长期刻意练习的结果,他们可能性格内敛,却因勤学苦练而写出遒劲有力的字;他们可能为人随性,却因追求法度而写出端庄工整的字,字展现的是“技”,而非“人”,将高超的技艺等同于高尚的人格,无疑是一种误读。
心境的变幻与情境的制约,使得字迹成为瞬间的情绪切片,而非恒定的性格标签。 “书为心画”固然有其道理,但“心”是流动的,而非静止的,同一个人,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心境下,写出的字迹也会大相径庭,李白在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的豪情中挥毫,其字必是奔放不羁的;而在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的愁绪里落笔,其字或显潦草、或带悲怆,苏轼的《寒食帖》便是最有力的例证,其书法在黄州贬谪的困顿与悲凉中,笔触起伏跌宕,情感真挚而压抑,这与他平日里旷达的文人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,若仅凭《寒食帖》便断言苏轼一生郁郁寡欢,无疑是片面的,字迹如同一面镜子,照出的往往是书写者那一刻的“心境”,而非其全部的“人格”,它捕捉的是情绪的浪花,而非人格的深海。
时代风气与审美取向的变迁,深刻地影响着书法的风格,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,而非纯粹的个人表达。 每个时代都有其崇尚的书法范式,唐代尚法,追求法度森严、气势恢宏;宋代尚意,强调个性解放、抒发胸臆;明清之际,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,书法也变得更加世俗化和装饰化,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人,其书法风格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,一位生活在唐代的书生,即便天性崇尚自由,其书法训练也可能受到“尚法”风气的影响,呈现出端谨的笔法,当我们看到一幅字时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,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,将字迹简单地归因于个人,而忽略了其背后宏大的文化背景,是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。
诚然,我们不能完全否定“字如其人”的合理性。 在某些情况下,一个人的字迹确实能反映出其性格的某些侧面,字迹工整、笔画清晰的人,可能做事严谨、有条理;而字迹潦草、龙飞凤舞的人,可能性格不羁、思维活跃,但这只能作为一种参考,一种概率性的推断,而非绝对的定律,人的性格是复杂多面的,而字迹的表达维度相对有限,用有限的笔墨去定义无限的人格,本身就是一种以偏概全。
“字如其人”是一种浪漫而美好的想象,它赋予了文字以人格化的魅力,在理性的审视下,我们必须承认,字迹是技艺、心境与时代共同作用的产物,它可以是书写者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可以是情绪瞬间的真实流露,也可以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集体符号,我们欣赏书法,不应仅仅满足于“以字论人”,更应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技巧、情感与文化内涵,真正的智慧在于,既能从字中品味书者的匠心与才情,又能清醒地认识到,那纸上墨痕,终究只是冰山一角,远不足以定义一个立体、丰富、活生生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