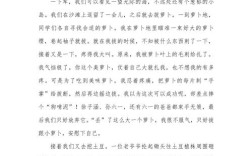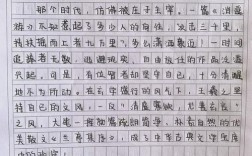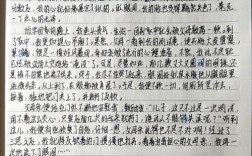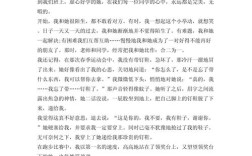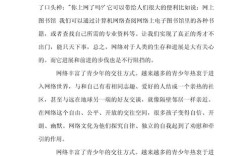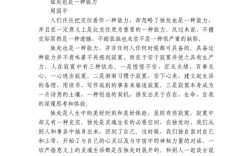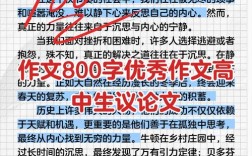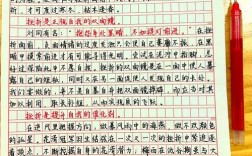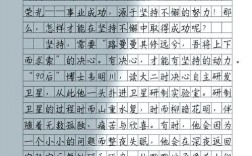一曲悲歌,千古绝唱——《霸王别姬》的多维解读
“力拔山兮气盖世,时不利兮骓不逝,骓不逝兮可奈何?虞兮虞兮奈若何!”当项羽在垓下营帐中,面对着爱姬虞姬,吟唱出这曲慷慨悲歌时,一个英雄的末路,一段爱情的绝唱,便已注定成为历史长河中最令人心碎的篇章。《霸王别姬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战败与殉情的历史故事,它更是一面映照人性、权力、宿命与时代变迁的多棱镜,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,折射出截然不同的精神内涵与悲剧色彩。
从历史真实到文学想象:一曲爱情的悲歌

《霸王别姬》的源头,是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那段简练而悲壮的记载:“有美人名虞,常幸从;骏马名骓,常骑之,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,自为诗曰:‘……’歌数阕,美人和之。”司马迁的笔触,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,项羽的“悲歌慷慨”是英雄末路的无奈,而虞姬的“和之”,则被解读为忠贞不渝的抉择,在历史的尘埃中,虞姬的形象逐渐从一个模糊的“美人”,升华为一个为爱情、为尊严而主动献身的烈女形象。
从元代杂剧到明清小说,再到现代京剧,无数艺术家为这个故事注入了血肉,尤其是京剧《霸王别姬》,通过程蝶衣“一招一式,一颦一笑”的演绎,将虞姬的柔美、刚烈与决绝刻画得淋漓尽致,剑光闪烁间,她不仅是项羽的爱姬,更是他精神世界的最后一道屏障,她的自刎,不是被动的牺牲,而是一种主动的成全——成全项羽的颜面,成全他们之间“不求生同衾,但求死同穴”的爱情誓言,在这一维度上,《霸王别姬》是一曲关于爱情与尊严的悲歌,它超越了战争的胜负,直抵人心最柔软的角落,让后人在千年之后,依然为这份凄美的决绝而动容。
从历史人物到文化符号:英雄末路的宿命
《霸王别姬》的魅力远不止于儿女情长,其核心,更在于对项羽这一悲剧英雄的深刻描绘,项羽,力能扛鼎,气吞山河,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将星,他刚愎自用,不善用人,最终落得个“乌江自刎”的结局,他的失败,既是性格的悲剧,也是时代的必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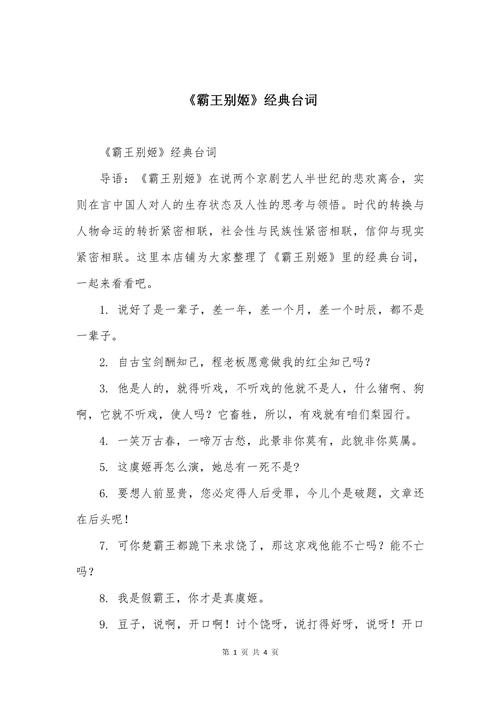
“霸王别姬”这一场景,是项羽一生荣辱的浓缩,它宣告了楚汉相争的终结,也揭示了英雄在历史洪流面前的无力感,四面楚歌,是敌军的围困,更是他内心世界的崩塌,当“时不利兮”成为现实,即便是“力拔山兮”的西楚霸王,也只剩下“奈若何”的苍凉,虞姬的死,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他英雄光环下的脆弱与孤独。《霸王别姬》也是一个关于宿命与选择的寓言,它探讨了在不可逆转的命运面前,个体尊严的坚守与毁灭,项羽的悲剧,在于他至死都未能明白,真正的“霸王”之位,不在于武力,而在于人心,他失去了天下,也最终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。
从经典文本到现代经典:时代的镜像与反思
如果说历史与文学中的《霸王别姬》是一曲定型的悲歌,那么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与陈凯歌执导的电影,则赋予了这一古老故事以全新的、具有现代性的解读,电影《霸王别姬》将历史背景移植到二十世纪的中国,通过京剧名角程蝶衣与段小楼近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,将“霸王别姬”的故事内化为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精神的缩影。
“霸王别姬”不再仅仅是楚汉争霸的典故,它成了程蝶衣人生的终极隐喻,程蝶衣,人戏不分,对艺术“从一而终”,对师兄段小楼(他心中的“霸王”)的爱恋也“从一而终”,当他最终在文革的批斗台上,看到段小楼为自保而揭发他、揭发菊仙时,他心中那座由艺术和情感构筑的“霸王”之殿轰然倒塌,那声凄厉的“你们都骗我!”,是程蝶衣对整个时代、对人性、对信仰的彻底幻灭。

电影的结尾,程蝶衣与段小楼再次合演《霸王别姬》,当虞宝剑的剑锋抵住程蝶衣的喉咙时,他选择了自刎,这一次,他不是虞姬,他是程蝶衣;他殉的不是项羽,而是那个被时代碾碎的、纯粹的“艺术”与“自我”,电影将个人的悲剧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,将“霸王别姬”这一文化符号,升华为对艺术、人性与时代荒诞性的深刻反思,它告诉我们,个人的命运,如同虞姬和项羽,永远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裹挟,个体的挣扎在时代的车轮面前,显得如此渺小而悲壮。
从《史记》的寥寥数笔,到京剧的婉转唱腔,再到电影的宏大叙事,《霸王别姬》的故事跨越千年,历久弥新,它既是儿女情长的悲歌,也是英雄末路的挽歌;既是关于宿命的探讨,也是对时代与人性的深刻拷问,它像一面镜子,映照出不同时代下,人们对于忠诚、背叛、尊严与毁灭的理解,当那曲《霸王别姬》的旋律再次响起,我们听到的,不仅是一个遥远的故事,更是对人性永恒困境的叩问——在命运的洪流中,我们该如何坚守自我,又该如何面对那无可避免的“别离”?这,或许正是《霸王别姬》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