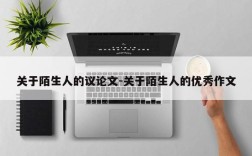寄情山水:安顿心灵的永恒归处
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”古老的智慧早已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点透,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丛林里,我们步履匆匆,内心被欲望、焦虑与喧嚣所裹挟。“寄情山水”便不再仅仅是文人墨客的风雅之事,更成为现代人安顿灵魂、寻找精神家园的必然选择,寄情山水,是一种姿态,一种哲学,更是一种在浮躁时代中保持内心澄澈与生命韧性的智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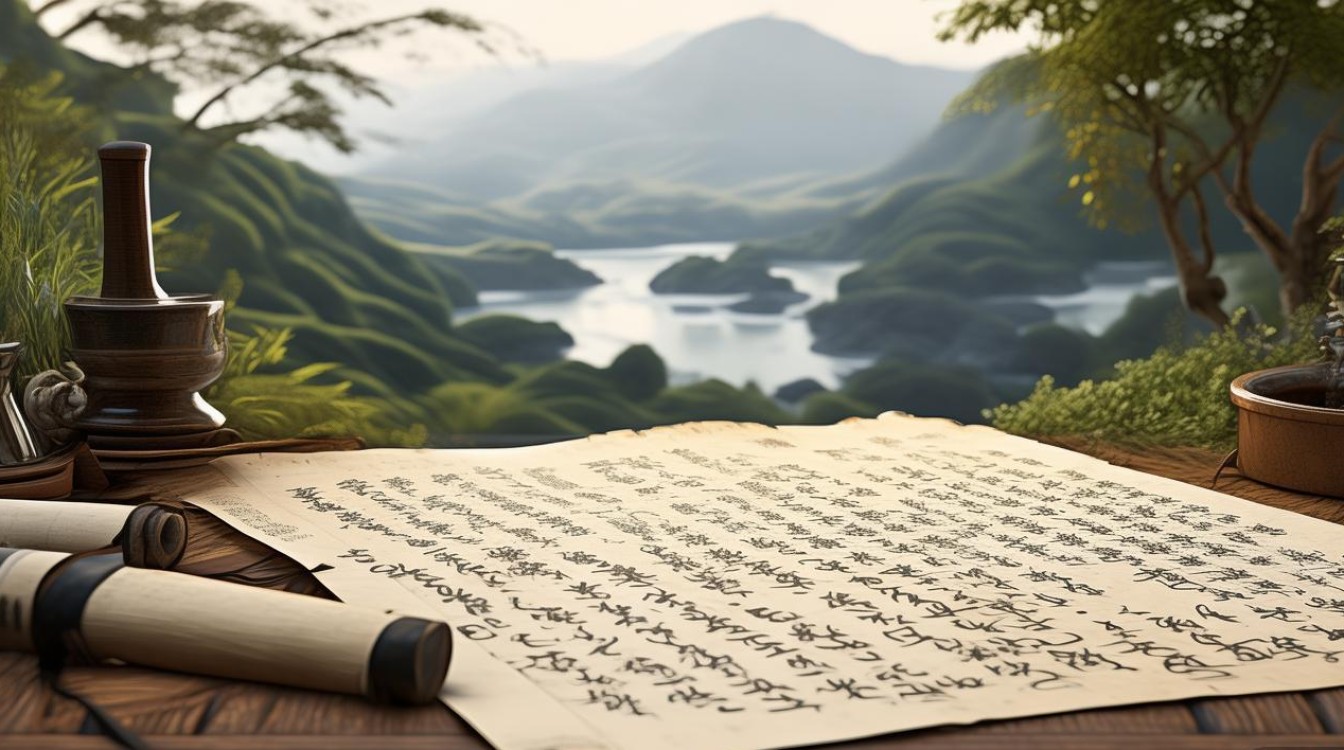
寄情山水,是挣脱尘网、回归本真的精神放逐。
陶渊明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,道出了千百年来无数人的心声,我们身处的社会,像一个巨大的“樊笼”,充满了无形的规则、无休止的竞争和物化的衡量标准,日复一日,我们容易在其中迷失自我,将生命的价值等同于外在的成就,而山水,以其原始、纯粹、未经雕琢的样貌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自身的镜像,当我们立于巍峨高山之巅,看云卷云舒,会感到个人的渺小与烦恼的微不足道;当我们行于潺潺溪水之畔,听流水潺潺,会体会到生命的流动与不息,山水无言,却以其磅礴与温柔,涤荡着我们内心的尘埃,让我们暂时卸下社会角色赋予的重担,回归到生命最本真的状态,找回那个未被世俗定义的“我”。
寄情山水,是涵养胸襟、砥砺品格的道德熔炉。
古人观山水,并非简单的游山玩水,而是在自然中感悟宇宙大道,砥砺个人品格,孔子“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”,是站得高、看得远的格局;范仲淹面对“衔远山,吞长江”的洞庭,抒发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胸怀,是山水所激发的博大与担当,山的沉稳坚毅,教会我们处变不惊,坚守信念;水的灵动柔韧,启示我们随机应变,顺势而为,在山水中,我们学会了谦卑,懂得了敬畏,也磨练了意志,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体验,将自然的品格内化为自身的精神气质,使我们的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与完善。
寄情山水,是寻求顿悟、激发创造力的灵感源泉。
“文章做到极处,无有他奇,只是恰好;人品做到极处,无有他异,只是本然。”艺术的最高境界是“恰好”与“本然”,而山水正是通往此境界的桥梁,王维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于静谧的山水中悟得禅意,开创了诗画合一的南宗画派;李白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”,在与自然的对视中,找到了精神的知己,写下了无数豪迈奔放的诗篇,山水的变幻莫测、气象万千,打破了我们固有的思维定式,为想象力插上翅膀,当我们身心俱疲、灵感枯竭时,投身于山水的怀抱,让清风拂面,让绿意盈眼,往往能在一瞬间茅塞顿开,获得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迪与创作冲动。
诚然,有人会说,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,我们足不出户便可通过屏幕“云游”四海,这种“云游”终究是隔靴搔痒,无法替代亲身的体验,真正的“寄情”,需要用双脚去丈量土地,用双眼去捕捉光影,用心灵去感受呼吸,它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与交融。
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寄情山水,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回归生活,它不是要我们逃离现实,而是要我们从山水中汲取力量,以更从容、更豁达、更坚韧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,当我们的内心有了可以安放的“山水”,外界的风雨便再难撼动我们精神的根基。
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,为自己留一片山,守一湾水,在那里,我们可以安放疲惫的灵魂,涵养博大的胸襟,点燃创造的火花,因为,那片山水,便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归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