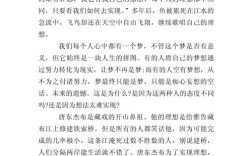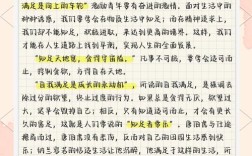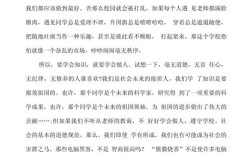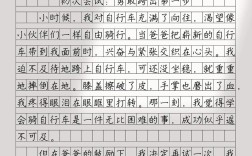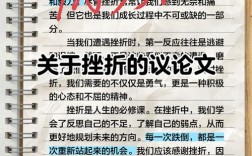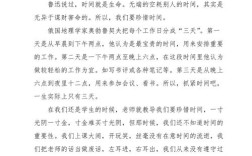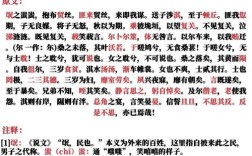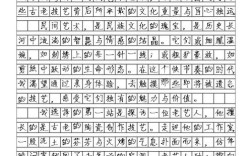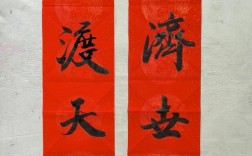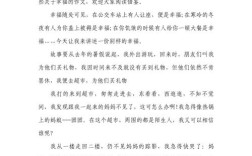诗意与孤寂:论林黛玉的悲剧魅力
在《红楼梦》的璀璨星河中,林黛玉无疑是最独特、最耀眼也最令人心碎的一颗星辰,她以其绝世的才情、孤高的品性和敏感多愁的性情,成为了中国文学长廊中一个永恒的符号,对黛玉的评价,历来褒贬不一,有人赞其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高洁,亦有人斥其“小性儿”、“多病身”的孤僻,若我们拨开世俗的偏见,深入其灵魂的内核,便会发现,林黛玉的悲剧,并非源于性格的缺陷,而是源于其“诗人”与“孤女”双重身份的深刻矛盾,这种矛盾,铸就了她不可复制的魅力,也注定了她香消玉殒的宿命。

林黛玉的悲剧根植于她“诗人”的灵魂。 她不是一个活在现实世界的凡人,而是一个用生命感受诗意的精灵,她的生命体验,与诗词紧密相连,她的喜怒哀乐,都化作了笔下的千古绝唱,在“沁芳闸桥边”的葬花之举,便是她诗人灵魂最极致的体现,她将飘零的落花视作与自己相似的命运,“一朝春尽红颜老,花落人亡两不知”,这不仅仅是对花的怜悯,更是对自身生命短暂、前途未卜的深刻预感,她的“多愁善感”,并非无病呻吟,而是诗人对世界极致敏感的体现,她能从“冷月葬花魂”的凄清景象中,读出生命的荒芜与孤独;她能在《葬花吟》的字里行间,唱响对命运不公的血泪控诉,这种将生命全然交付给诗意的存在方式,让她与追求功名利禄、讲究人情世故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,她的世界太纯粹,太干净,容不下半点污浊与虚伪,当她身处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刀霜剑严相逼”的大观园时,她的诗人灵魂注定了要与这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的环境产生剧烈的碰撞,最终遍体鳞伤。
林黛玉的悲剧加剧于她“孤女”的身份。 诗人赋予了她敏感的内心,而“孤女”的身份则给这颗敏感的心套上了沉重的枷锁,她自幼丧母,不久又痛失父亲,寄人篱下的经历,让她时刻处于一种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的状态,这种身份上的弱势,让她不得不时刻警惕,步步为营,她的“小性儿”,她的尖酸刻薄,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,她通过试探贾宝玉的感情,通过挑战封建礼教的权威,来确认自己在这座金丝笼中的价值与位置,她与薛宝钗的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”,看似冰释前嫌,实则是两个同样聪慧的女性在复杂环境下的相互试探与妥协,黛玉深知,在这个以家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世界里,她没有强大的家族作为后盾,唯一的依靠便是那份看似虚无缥缈的爱情,她对宝玉的爱,既热烈又执着,既甜蜜又充满焦虑,这种因孤寂而生的不安全感,如同一根无形的刺,时时刺痛着她的心,加速了她走向悲剧的步伐。
正是这“诗人”与“孤女”的双重身份,成就了林黛玉不朽的魅力。 她的孤高,源于诗人的洁身自好;她的敏感,源于孤女的自我保护;她的才情,则是她对抗整个冰冷世界的唯一武器,她用自己的诗词,在那个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时代,为女性的情感与思想开辟了一片独立的天地,她不像薛宝钗那样“随分从时”,懂得迎合世俗;也不像史湘云那样“英豪阔大宽宏量”,活得洒脱自在,黛玉的悲剧性,恰恰在于她的“真”——她不肯戴上虚伪的面具,不肯向世俗的规则低头,她活得真实,爱得纯粹,死得决绝,她用整个生命去实践了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誓言,最终在宝玉大婚的锣鼓声中,焚烧掉自己的诗稿与情感,回归那“太虚幻境”的清净之地。
林黛玉的悲剧,是一个诗人的灵魂在封建末世的现实困境中必然的陨落,她的“诗人”属性让她超越了凡俗,看到了世界的本质;她的“孤女”身份则让她在现实中步履维艰,痛苦挣扎,这双重身份的交织,构成了她性格的全部复杂性与深刻性,她不是完美的,但她是真实的;她不是幸福的,但她是自由的,她的存在,如同一面镜子,照见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,也照见了人性中最真挚、最动人的情感,林黛玉,这个用生命写诗的女子,她的魅力与悲剧,将永远在文学的天空中,散发着凄美而动人的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