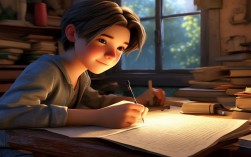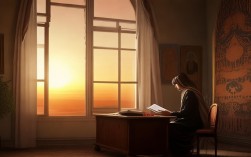雅俗之辩:在融合中寻求文化的新生
“雅”与“俗”,这对贯穿中国数千年的文化范畴,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,共同构成了我们精神世界的完整图景,从《诗经》的“风、雅、颂”,到唐诗宋词的阳春白雪与市井小调,再到如今高雅艺术的殿堂与流行文化的喧嚣,雅俗之争从未停歇,若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,视作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,便陷入了认知的误区,在我看来,雅与俗并非势不两立,而是相生相成、动态演变的辩证统一体,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,我们更应超越雅俗之辩的二元对立,在理解、尊重与融合中,探寻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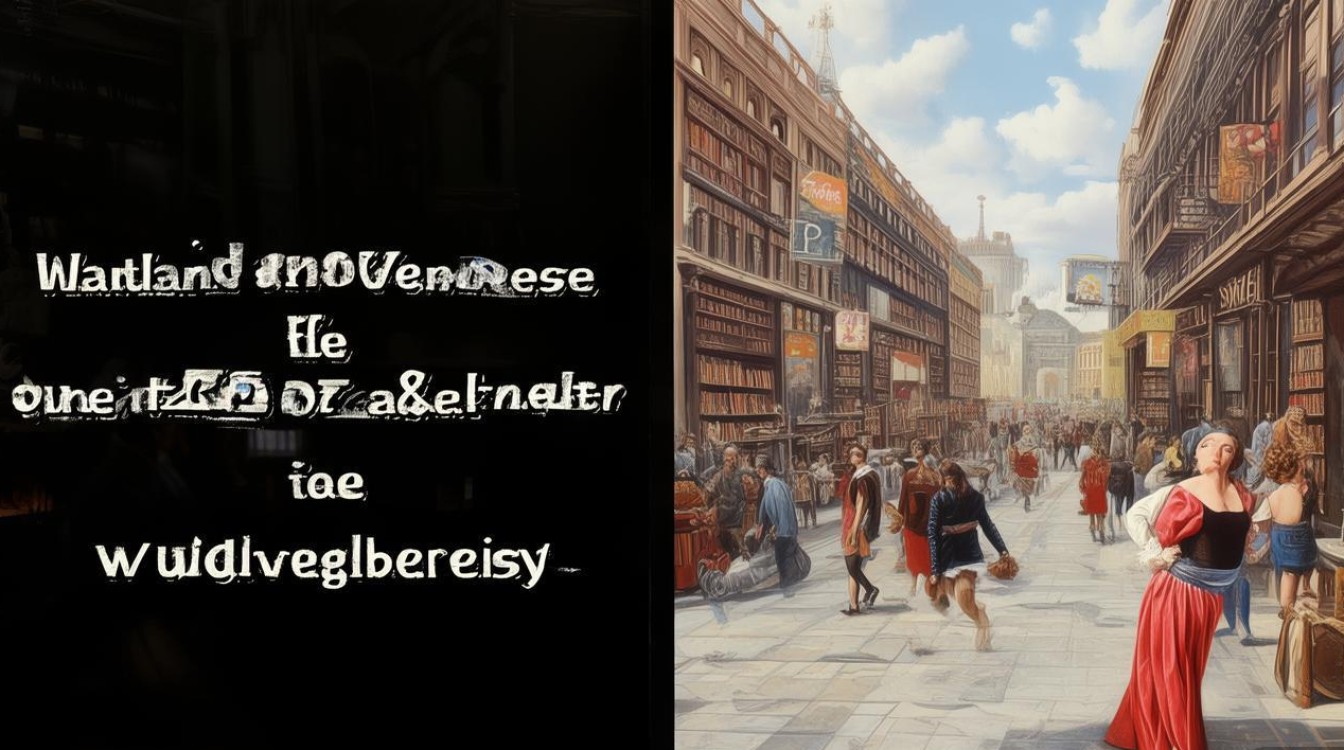
雅与俗的界定并非永恒,而是随时代变迁而流动的相对概念。
“俗”者,通俗也,源于民间,根植于大众的生活实践,它是最鲜活、最直接的情感表达,是未经雕琢的璞玉,从汉乐府的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”,到宋元话本的市井奇闻,再到今日的短视频、网络神曲,俗文化以其强大的亲和力与传播力,成为时代脉搏最直观的跳动,它记录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,反映着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,是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基石。
“雅”者,典雅也,是文人对“俗”的提炼、升华与再创造,它经过时间的淘洗与艺术的打磨,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与思想上的深邃,从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到贝多芬的交响乐,从古典园林的曲径通幽到抽象派的色彩哲学,雅文化构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崇高殿堂,引领着审美向更广阔、更深刻的境界探索。
雅俗之间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,昔日的“阳春白雪”可能曾是昔日的“下里巴人”。《诗经》中的“国风”本是民间歌谣,却被孔子奉为经典,登上了大雅之堂,宋词在诞生之初,被视为“诗余”,是难登大雅之堂的“艳科”,最终却与唐诗并驾齐驱,成为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,反之,许多今日被视为“雅”的艺术形式,在其萌芽阶段也曾是“俗”的代表,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雅与俗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,俗是源头活水,为雅提供不竭的滋养;雅则是河道,引导着文化的流向,使其更具深度与广度。
雅俗交融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必然趋势。
一种文化形态若要永葆活力,必须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,敢于打破雅俗的壁垒,实现相互借鉴与融合,雅为俗提供精神内核与审美范式,使其摆脱低级趣味,提升格调;俗为雅注入新鲜血液与时代气息,使其免于僵化枯竭,贴近生活。
纵观艺术史,无数杰作都是雅俗交融的结晶,元曲的杂剧,将文人雅士的才情与市井百姓的语言、故事巧妙结合,开创了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,敦煌壁画,既有宗教绘画的庄严神圣(雅),又融入了鲜活的世俗生活场景与人物形象(俗),使其成为一部立体的“中古社会的百科全书”,在当代,这种现象更为普遍,优秀的电影导演,既能运用精妙的镜头语言(雅),又能讲述引人入胜的市井故事(俗);成功的流行音乐人,既能借鉴古典音乐的旋律结构(雅),又能用现代的节奏与唱腔(俗)引发大众共鸣,这种“雅俗共赏”的艺术,因其既能满足精英阶层的审美期待,又能被普通大众所接受,从而获得了最广泛的生命力。
我们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,超越雅俗之辩,拥抱文化的多样性。
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,我们时常看到对“俗”的鄙夷和对“雅”的盲目追捧,或是走向另一个极端,将“俗”奉为圭臬,解构一切崇高,这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,真正的文化自信,不是固守某一端,而是拥有欣赏和容纳不同层次文化形态的胸怀。
我们不必强求所有人都走进音乐厅欣赏交响乐,也不应鄙夷在街头巷尾哼唱流行歌曲的乐趣,文化生态如同自然生态,需要高山,也需要平原;需要参天大树,也需要无名花草,雅文化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技艺,为我们提供了精神的灯塔;俗文化以其鲜活的气息和广泛的参与,构成了文化的汪洋大海,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。
面对雅与俗,我们应摒弃非此即彼的傲慢与偏见,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,当努力追求“通俗而不庸俗,高雅而不孤高”的境界,让文化既有泥土的芬芳,又有星空的璀璨,作为文化的欣赏者,当以更宽广的视野去品味,既能从《高山流水》中感受知音的千古绝唱,也能从一首动人的民谣里触摸到时代的温度。
雅俗之辩,最终指向的应是文化的繁荣与人性的丰满,唯有让雅与俗在碰撞中对话,在交融中前行,我们的文化才能在传承中创新,在开放中壮大,真正实现生生不息的新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