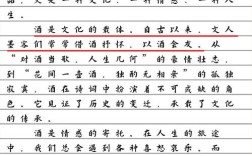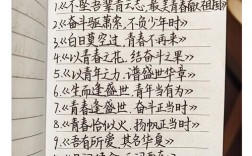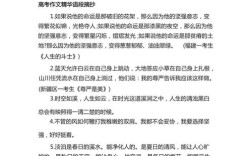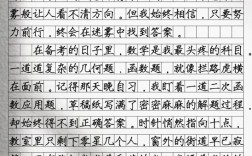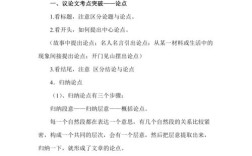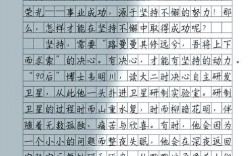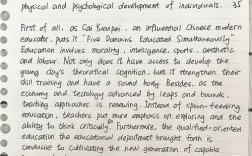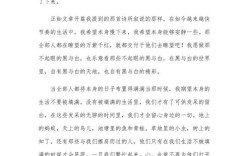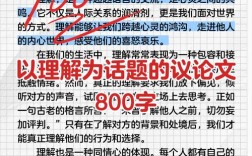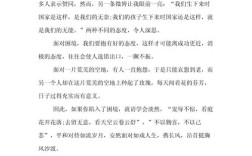鸿门宴:一场人性与权谋的千古棋局
“鸿门宴”,这三个字在中国文化中早已超越了其作为一场宴席的本身,它化身为一个符号,一个象征,代表着充满杀机、危机四伏的险境,也揭示了在历史洪流中,人性、权谋与抉择的复杂博弈,司马迁以如椽巨笔,将这场宴会写得波澜壮阔,扣人心弦,当我们拨开刀光剑影的迷雾,审视这场千古棋局,会发现其胜负的关键,并非在于项羽的“妇人之仁”,而在于刘邦的“知人之明”与“顺势而为”,以及一场关于人性弱点的深刻寓言。

鸿门宴的胜负手,不在于项羽的“仁”,而在于刘邦的“智”。
长久以来,人们将项羽的失败归咎于他“鸿门宴上放走刘邦”的“妇人之仁”,这种看法过于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,项羽的“仁”,更多是一种源于贵族式骄傲的、缺乏政治远见的“不忍”,他信奉的是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个人英雄主义,他无法理解,也看不起刘邦那种“厚黑”的生存法则,在项羽看来,刘邦不过是自己手下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“沛公”,杀他易如反掌,但此举可能引来非议,有损自己“义”的形象,这并非真正的仁慈,而是一种基于个人好恶和虚荣的犹豫。
反观刘邦,他展现出的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,赴宴前,他低声下气,亲赴鸿门,向项羽示弱,称臣谢罪,成功瓦解了项羽的杀心,宴席之上,他面对项庄舞剑的杀机,面不改色,从容应对,更重要的是,他身边有一个堪称“神助攻”的团队:张良的运筹帷幄,樊哙的忠勇果敢,项伯的“内鬼”式相助,刘邦的成功,并非一己之力,而是他善于识人、用人,并让整个团队发挥最大效能的结果,他深知自己不如项羽勇猛,便用智慧和隐忍来弥补,这种“将能而君不御”的领导艺术,正是项羽所缺乏的,鸿门宴的结局,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英雄对无赖的审判,而是一个战略家对莽夫的胜利。
鸿门宴是项羽性格缺陷的集中暴露,是其悲剧命运的缩影。
项羽的性格,如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剑,他的勇武、自信、坦荡,让他成为万人敬仰的西楚霸王;但他的刚愎自用、优柔寡断、政治幼稚,也最终将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,鸿门宴是这些缺陷的放大镜。
刚愎自用,使他听不进范增的多次暗示,范增“数目项王,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”,已是极其明确的信号,但项羽却“默然不应”,他过于自信,认为凭自己的威仪就能震慑刘邦,无需采取下策,这种对个人能力的盲目崇拜,让他错失了最佳的战机。
政治幼稚,让他无法看清人心的向背与局势的走向,他迷信武力,认为只要击败刘邦,天下便太平,他不懂“天下苦秦久矣”的民心所向,也不懂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”的政治规律,他将刘邦视为一个需要被消灭的对手,而不是一个需要被征服的政治力量,这种思维,导致他在分封诸侯时埋下祸根,也为日后刘邦的崛起提供了土壤。
优柔寡断,则是他性格中最致命的弱点,在杀与不杀之间,他反复摇摆,最终被刘邦的几句软话和樊哙的“义正辞严”所蒙蔽,一个在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将军,在政治决策上却如此迟疑,这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帝王,鸿门宴上的犹豫,为他日后乌江边的自刎埋下了伏笔。
鸿门宴是一场深刻的人性实验,揭示了不同境遇下的人性选择。
在这场宴席上,每个人物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,而这些选择,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
刘邦,选择隐忍,他可以为了生存放下一切尊严,这种“能屈能伸”的生存哲学,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往往是最有效的武器。
项羽,选择骄傲,他宁愿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力量,也不愿相信他人的计谋和忠告,他的骄傲让他失去了最宝贵的盟友范增,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。
范增,选择绝望,他作为项羽的“亚父”,尽心竭力,却屡次被无视,当玉玦不被理会,当项庄的剑被樊哙阻挡,他预见到大势已去,只能愤然离席,拔剑撞玉斗,发出“竖子不足与谋”的悲叹,范增的离去,象征着项羽阵营的智慧核心开始崩塌。
樊哙,选择忠诚与勇猛,他闯帐斥责项羽,看似鲁莽,实则是在为刘邦争取时间和道义,他的行为,既有对刘邦的绝对忠诚,也展现了底层英雄的豪迈与义气,从侧面反衬了项羽阵营内部的分裂与不纯。
鸿门宴,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其惊心动魄的程度,丝毫不亚于千军万马的厮杀,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,更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幽暗,权谋的精妙与残酷,项羽的失败,败给了自己的性格,败给了刘邦的团队,更败给了那个时代所选择的历史方向,刘邦的胜利,则证明了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,一时的勇武并非万能,深远的战略、识人的眼光、以及在逆境中生存的智慧,才是笑到最后的真正筹码,千百年后,当我们再次谈论鸿门宴,我们谈论的,不仅是一场宴席的胜负,更是一场关于如何为人、如何处世、如何驾驭命运的永恒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