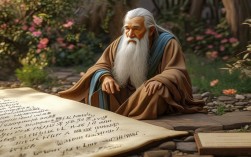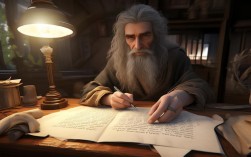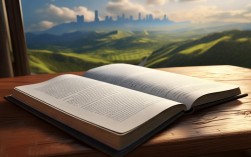围墙之内,亦是围墙之外
从秦始皇筑长城以御匈奴,到寻常百姓家院的高墙矮篱,从学校、监狱的物理屏障,到人心、思想的无形边界,“围墙”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存在,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始终,它既是物理的实体,也是精神的象征,它守护安宁,却也禁锢思想;它划分疆界,却也滋生隔阂,我们身处围墙之内,又时常渴望围墙之外,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。

围墙是秩序与安全的基石。 任何社会、组织乃至个人,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来生存和发展,城墙,守护了一座城池的安宁;国界,划分了不同国家的主权与责任;家庭的院墙,为成员提供了一个私密、温馨的港湾,围墙之内,我们建立起规则,形成共识,创造文化,没有围墙的保护,个体将如浮萍般漂泊,随时可能被外界的风浪所吞噬,从这个意义上说,围墙是文明的“襁褓”,它为成长提供了必要的庇护,让秩序得以建立,安全得以保障。
当围墙变得过高、过厚,它便会异化为禁锢与隔阂的牢笼。 心灵的围墙,一旦筑起,便是最难逾越的障碍,一个固步自封的人,用偏见和傲慢筑起高墙,将自己与外界的新知、多元的观点隔绝开来,最终在思想的孤岛上日渐僵化,一个故步自封的民族,若以“天朝上国”的心态为墙,便会错失与世界交流互鉴的机遇,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落后,鲁迅先生笔下“铁屋子”里沉睡的人们,正是被无形的传统与愚昧的围墙所禁锢,无法醒来,这道墙,看似保护了“安稳”,实则扼杀了“生机”。
更为危险的是,围墙常常成为划分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的工具,滋生偏见与冲突。 历史上,种族的、宗教的、文化的围墙,曾引发了无数战争与悲剧,纳粹用意识形态的围墙将犹太人划为“异类”,导致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,网络上“信息茧房”的围墙,让人们只愿意看到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,不同声音被自动屏蔽,社会共识被撕裂,对立情绪日益加剧,这道墙,将世界切割成一个个相互敌视的碎片,阻碍了理解与和平的可能。
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无处不在的围墙?答案并非是彻底拆除,而是学会如何建造与跨越。 我们需要智慧来建造一道“通透的围墙”,这道墙,既能守护我们内心的秩序与安全,又设有“门窗”,允许阳光、空气和思想的自由流通,它意味着在坚守原则的同时,保持开放的心态;在保护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同时,尊重并欣赏他人的多样性。
更重要的是,我们需要勇气去跨越那些不必要的、有害的围墙,跨越围墙,意味着主动去接触不同的文化,去倾听异见的声音,去挑战自己的固有认知,它要求我们走出舒适区,以谦卑之心拥抱世界,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:“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。”这其中的关键,正在于打破隔阂的围墙,在欣赏与互鉴中,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
归根结底,围墙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,它是一把双刃剑。 它可以是守护家园的臂膀,也可以是束缚思想的枷锁;可以是划分疆界的界碑,也可以是沟通桥梁的起点,真正重要的,是我们建造围墙的初衷,以及我们对待围墙的态度,我们应当成为围墙的主人,而非奴隶,在享受围墙带来的安全感时,时刻警惕它可能带来的封闭性;在拥有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时,不忘抬头看看墙外的广阔天地。
围墙之内,是我们的根基与家园;围墙之外,是我们的未来与远方,唯有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,我们才能既脚踏实地,又仰望星空,在守护与开放之间,走出一条通往自由与和谐的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