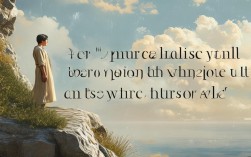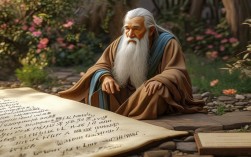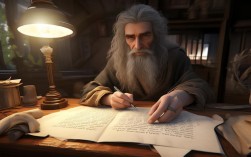霸王别姬,悲歌一曲论项羽
历史的长河中,总有一些身影,如流星般璀璨,却转瞬即逝,留下无尽的唏嘘与沉思,西楚霸王项羽,便是这星河中最耀眼也最悲情的一颗,他力能扛鼎,气吞山河,于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,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;他亦刚愎自用,妇人之仁,最终在垓下四面楚歌中,上演了霸王别姬的千古悲剧,论项羽,我们无法简单地用“成功”或“失败”来定义他,他更像是一面棱镜,折射出人性中光明与黑暗、英雄与凡人的复杂光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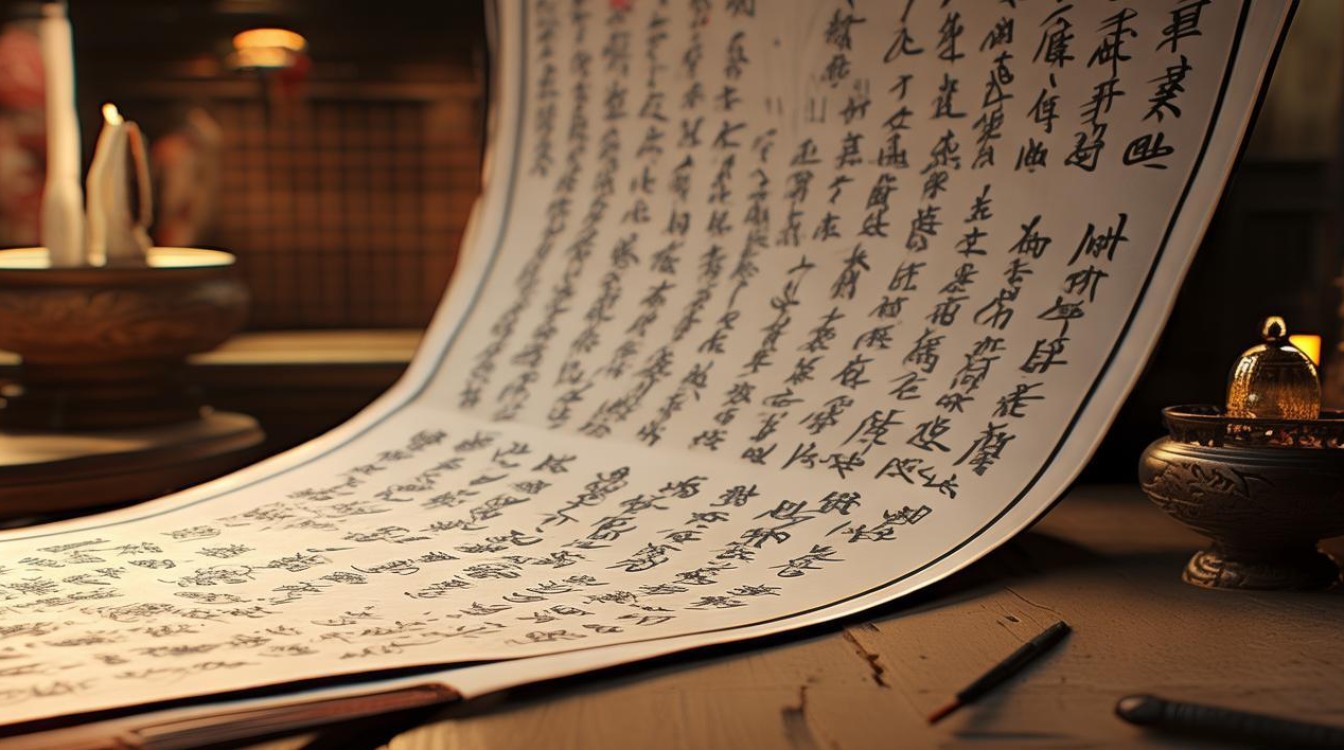
项羽的悲剧,首先源于其“英雄”与“霸主”角色的内在冲突。 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军事天才,却非一位合格的政治领袖,巨鹿之战,他“皆沉船,破釜甑,烧庐舍,持三日粮,以示士卒必死,无一还心”,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与勇猛,让他成为了六国诸侯的精神图腾,战场上的项羽,是战神,是无敌的化身,当战场的硝烟散尽,需要他治理天下、安抚百姓时,他的“英雄”气质便成了“霸主”的致命伤,他信奉武力征服,而非人心归附,入咸阳,他“烧秦宫室,火三月不灭”,大失民心;分封天下,他凭个人好恶,将故地分予亲信,将刘邦封于偏远的汉中,埋下了日后纷乱的种子,他不懂“攻心为上”的道理,只懂得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豪横,这种将军事才能无限放大,而将政治智慧无限缩小的错位,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开疆拓土的猛将,而非一个开创盛世的君主。
项羽的悲剧,其次在于其性格中的致命缺陷——刚愎自用与妇人之仁。 范增,这位被项羽尊为“亚父”的谋士,堪称其事业的“定海神针”,鸿门宴上,范增“数目项王,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”,意图借机除掉刘邦这个心腹大患,项羽在项伯的游说和自身的自负下,犹豫不决,错失良机,他宁愿相信所谓的“兄弟情义”,也不愿相信老谋深算的范增,当陈平施反间计,范增被猜忌而愤然离去时,项羽的霸业便已失去了最重要的智囊,这便是他的“刚愎自用”,他又处处显露出“妇人之仁”,鸿门宴上,面对刘邦的卑微求和,他动了恻隐之心;面对樊哙的闯帐怒斥,他非但没有降罪,反而“壮士”之,并赐酒赐彘,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摇摆不定,对敌人的仁慈,恰恰是对自己事业的残忍,政治是冷酷的博弈,项羽却用江湖义气来处理天下大事,其败亡,性格使然。
若项羽仅仅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,历史便不会对他如此偏爱。 他的伟大之处,在于其人格魅力中那份纯粹与真诚,那份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的尊严,垓下之围,八百江东子弟兵随他杀出重围,当他逃至乌江边,亭长劝他“江东虽小,地方千里,众数十万人,亦足王也”,他却苦笑道:“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,今无一人还,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,我何面目见之?”这番话,展现了他超越生死的责任感与荣誉感,他不愿苟且偷生,不愿看到追随他的人因他而尽殁,他选择将头颅赠予旧友,以换取部下的性命,这种悲壮的结局,非但无损其英雄形象,反而为其传奇增添了最厚重的一笔,他不是输给了刘邦,而是输给了他自己的骄傲与尊严。
项羽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。 他是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的顶天立地的英雄,也是“天亡我,非战之罪”的刚愎自用的失败者,他的失败,是个人英雄主义在历史洪流中的必然落幕;他的伟大,在于他用生命诠释了何为“霸王”的风骨与气节,他如同一柄锋利无匹却不知保养的宝剑,虽能斩断千军万马,却也因自身的坚硬而最终折断。
历史没有如果,我们无法假设项羽若能虚心纳谏、宽厚待人,历史将会如何改写,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正是因为这份不完美,项羽才成为了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,他的故事,如同一首荡气回肠的史诗,警示后人:真正的强大,不仅是力拔山兮的勇武,更兼有运筹帷幄的智慧与海纳百川的胸襟,霸王别姬,一曲悲歌,唱尽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更迭,更是一个英雄在时代浪潮中,最绚烂也最无奈的宿命。